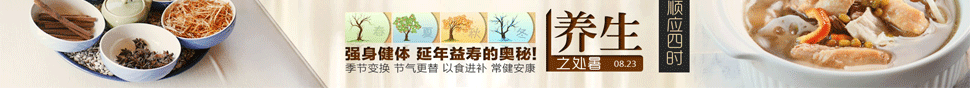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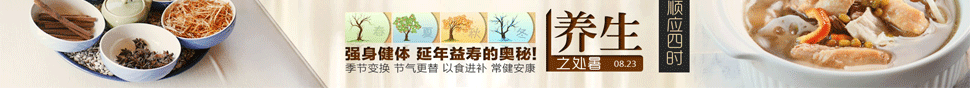
□陈玉华
汪曾祺先生的一生中,有几个重要的人生驿站,出生地在高邮,求学在西南联大,工作和安息地在北京,特殊时期因打成右派被发配到张家口劳动改造。继去年汪迷部落文学社组织了“寻访汪曾祺足迹”云南行、“寻访汪曾祺足迹”张家口大同行之后,我带着一本汪老的散文集,与17位寻访团成员一起踏上了寻访汪曾祺先生足迹的北京之行。
汪老曾因工作和生活的变迁在京城辗转七个居所。他住的每个地方和他创作的作品有什么联系、有什么故事,对他的文学作品有什么影响,是我们北京寻访的初衷。汪老最初的住处是北京市文联宿舍(东单三条29号)。第二个住处北京市民间文艺家研究会宿舍(河泊厂13号)。三是在北京新文化街附近的文化胡同8号。四是在国会街5号的四合院。第五个地方是在甘家口,阜城路南一楼5门9号,他在这个地方住的时间最长,从66年初到83年夏天。第六个住处是在作家云集的蒲黄榆9号楼1号。第七个住处是在福州馆前街(虎坊桥)4号楼。虎坊桥是汪老晚年最后一个居住地,他在此居住了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时间,但这里是汪老一生中居住最满意的一个居所,因为这里有一个十平方米的独立书房,而且置放了一张大书桌,随时可以写写画画。
虎坊桥,是此行的首站。这里是汪曾祺先生笔下多次描绘的京城一隅。走在虎坊桥附近的小巷中,我仿佛能听到汪老与街坊邻居亲切交谈的声音,看到他在街头巷尾观察生活、汲取创作灵感的身影。在虎坊桥高家寨胡同,我们与提前到达的汪朗夫妇汇合。汪朗老师边走边向寻访团成员讲解了汪老生前住在这里的点点滴滴,小区出口的胡同以前是个小市场,当年汪老或下楼溜达、或购买食材时总喜欢与商贩们闲聊,这里的烟火气如同老家东大街的情景再现,常常勾起汪老对家乡的思念。
也许汪老在天有灵,知道家乡的汪迷们来看他了,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,我们恍惚间感到这雨滴就是汪老开心的泪花。汪老喜雨,他在散文《昆明的雨》中,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雨中的一切,春雨和秋雨的不同,他描述了雨滴在雨伞上的声音,雨滴在叶子上的声音,雨落在草地上的声音……北京的春雨跟南方的不同,干脆而不缠绵。冒着淅沥沥小雨,汪朗老师带着大家走到了附近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旧址拍照打卡,当年由汪老牵头负责改编的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就是在此诞生的,站在俱乐部大戏院广场,阿庆嫂“智斗”中的经典唱段隐约耳中响起:垒起七星灶,铜壶煮三江。摆开八仙桌,招待十六方。来的都是客,全凭嘴一张。相逢开口笑,过后不思量。人一走,茶就凉。有什么周详不周详……
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此行第二站。在这座文学殿堂里,珍藏着许多现代文学大家的珍贵手稿和遗物,其中就有汪曾祺先生的部分作品。当看到汪老熟悉的字迹,那些跳跃而有生命力的文字,再次用它们的深情厚意感动了我们。
接着我们受邀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。这里是汪曾祺先生多部作品得以问世的地方。走进这座充满文化气息的建筑,我仿佛穿越到了那个文学繁荣的年代。在出版社的档案室里,我找到了汪老的一些出版记录,那些泛黄的纸张记录着汪老作品的诞生和流传。我想象着当年汪老与编辑们交流探讨的场景,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阵的感动。
最后一站,福田公墓。这里是汪曾祺先生长眠的地方。我们带着鲜花、带着汪老喜欢的烟和酒,还特地从家乡带着汪老生前喜欢的下酒小菜蒲包肉、盐水鹅、咸鸭蛋,来到了汪老的墓前。墓碑上刻着“高邮汪曾祺、长乐施松卿之墓”,简洁而庄重。我们轻轻地摆放好祭品,向这位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有趣的灵魂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站在墓前,回想起汪老的文字,那些关于生活、关于人性、关于美的思考,此刻在我心中回荡,仿佛汪老的精神依然在世间流传。
声明: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,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,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。邮箱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puhuanga.com/phjf/14425.html